记得2004年暑假,我有幸赴台湾清华大学跟随人类学家陈祥水教授做短期的学习和研究。在那段密集知识输入的时光里,我辗转多地不停参访、调研,还参与田野调查,获得感满满。20年之后生活和工作兜兜转转,虽未再从事人类学相关的工作,但在此时遇上《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物的灵韵与人的故事》这本书,被作者讲述故事的天赋和对人类学博物馆的敏锐观察与思考所折服,勾起美好往事的同时,也不免引出一些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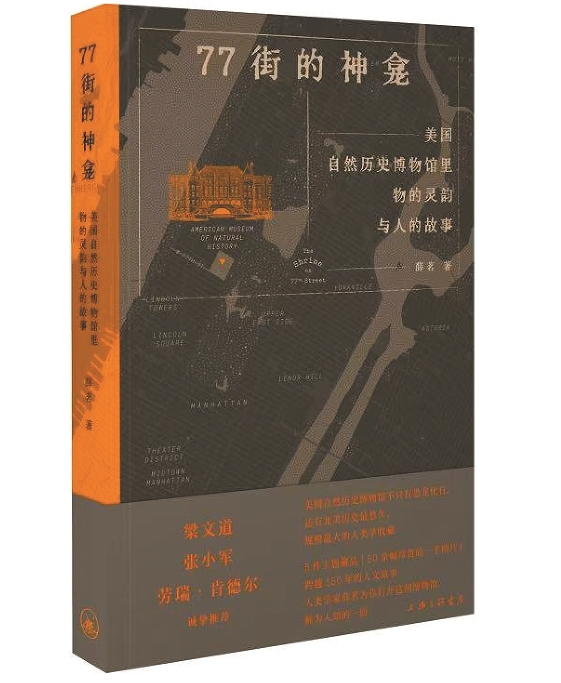
《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物的灵韵与人的故事》 薛茗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
何为“灵韵”:物的生命史与人的故事
坐落于纽约上西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由多座博物馆构成的博物馆群,它们以天文、矿物、古今生物标本收藏闻名于世,大家所熟知的系列电影“博物馆奇妙夜”正是取景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因而这里的恐龙化石和动物标本似乎更受人瞩目。其靠近纽约77街的人类学展厅展示着北京的皮影、西藏的唐卡,甚至还有占据一面墙的阿兹特克太阳石——正是书中的这座“77街的神龛”。事实上,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本书选择用一件藏品或展品引出一个有关人类学博物馆主题的叙事方法,思考深刻又表达生动。
书名副标题中的“灵韵”一词,本意指艺术作品的一种独特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它是一种笼罩在艺术作品之上的神秘氛围,使作品具有一种令人敬畏、吸引人的精神品质。观众在欣赏有灵韵的作品时,会产生一种敬畏和惊叹的情感,仿佛作品有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了“灵韵”的重要概念。他用“灵韵”来描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传统艺术作品具有灵韵,例如古典绘画、古老的雕塑等,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产生,灵韵与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不可接近性有关。传统艺术的灵韵是在仪式和崇拜中产生的,作品在被观赏时有一种神圣的距离感。
从这层概念出发,本书作者提出了一道思考题,也是我们展览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博物馆里的佛像、面具和神衣等具有一定的“灵性”,它们既不像其他展厅中的标本化石,也不完全等同于佛寺庙宇中被人供奉朝拜的神圣之物,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呢?博物馆会是它们的终点吗?《77街的神龛》给出了答案——物的灵韵,离不开人的故事。现代人类学的收藏与展览不是为了留下某种文化的“最后一刻”并将其封存在展柜里,而是用一件器物去讲述人的生命史与物的生命史相互交织的故事。在“一张唐卡的旅程”这一章,作者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还原了唐卡如何出自一位中国青海省热贡县的女画师之手,“为《冥想观音》起稿时,可能是伦措自己心境最不平静的时期。她的新角色——妻子、儿媳、一岁婴儿的母亲,以及她一直承担的家中‘大女儿’的责任,让她很难找到时间坐到画布前。但凭借当年决定成为唐卡画师的坚定,伦措用这张《冥想观音》向其他人证明,女性画师,哪怕是刚刚生了孩子的女性画师,也可以和男性画师一样创造出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字里行间中是女性的热爱与坚守,也让人感动于博物馆里人类学家工作的意义。
由此想到笔者工作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展厅里,曾经也多次举办过唐卡艺术展。过往的呈现模式多聚焦于作品艺术表象的雕琢,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唐卡艺术的视觉魅力,然其背后所潜藏的丰富人文宝藏——或是创作者的匠心独运、或是收藏者的珍视传承、又或是策划者的精心布局,却被不经意地遮蔽于艺术的华彩之后,未能充分彰显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诚然,不同的展览语境与目标定位会催生出各异的策展路径,但当我们深入反思,会发觉过于注重展品的直观呈现,而忽视了其背后所凝聚的人类情感、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的深刻内涵,何尝不是展览的一种缺失。
如何阐释:“在场性”抑或“在对岸”
在博物馆的世界里,阐释犹如一把双刃剑,其重要性在“博物馆化”的进程中愈发凸显。博物馆化起始于对物的收藏,当物品脱离原生地、文化与经济背景,被选择、收集并移植到博物馆时,其语境被剥离,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并重新构建。物的价值在时代浪潮中日益多元,而价值赋予的手段也因时代更迭而被赋予不同解读。这一过程使得阐释成为连接展品与观众的关键桥梁,没有恰当的阐释,观众难以理解展品背后的深邃内涵。
在“空中行船”一文中,人类学家米德不愿循规蹈矩,她的野心是“让纽约的观众既对太平洋原住民的多样性有一个整体了解,又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对新型建材的大胆使用不但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艺术馆里颇为成功的极简设计在人类学展馆里反而弄巧成拙。无论是模仿海水而铺的绿松石蓝色地板,还是为了模拟热带阳光而悬挂的千余盏日光灯,都没有赢得观众的芳心,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材料和太平洋岛屿的本土环境差异过大,观众根本不可能“沉浸”到当地的生活氛围中,仅六年后,展馆便关闭重修。太平洋展厅所面临的将人类学知识“翻译”成公共展览的困境,涉及到“在场性”与“在对岸”两种阐释风格的探讨。米德的“在场性”,源于她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不懈的书写,她以“从我坐着的地方讲起”的方式,试图引领读者走进她的田野,感受真实的情境。然而,与之相对的学院派人类学写作则站在“对岸”,以一种上帝视角进行概括、抽提、归纳与演绎,作者隐匿自身痕迹,以维护学术作品的理性与权威。这种差异导致米德的作品虽受普通读者喜爱,却在学术界饱受孤立。
进一步来看,米德将“在场性”转化为“沉浸式”展览体验的尝试利弊共存。从积极方面而言,她希望观众能像她一样“到场”,亲身体验太平洋海岛的文化与自然环境。但现实却存在诸多阻碍,对于米德来说是真切回忆的场景,观众只能凭借想象去构建,而展厅的种种元素,如灯光颜色、展柜材质、展品样貌等,可能会限制观众的想象空间,与观众自发代入的意境大相径庭。就如同经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难以尽如人意一样,展厅设计中也存在着矛盾动机,既期望观众“身临其境”深入特定文化内部,又希望观众能从宏观上把握展厅全貌。米德的女儿也指出,尽管展厅背后逻辑美好,但现实中奇异材料难以整合为统一叙事。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在策展时经常会灵魂拷问的问题:即使借助先进技术打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效与沉浸式体验,如LED射灯、360度投影仪、VR技术等,这是否真的能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展品、艺术家或一种文化?会不会只是陷入感官愉悦的“马戏团”陷阱,而智识却毫无增进?
如何定位:以物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
如果说米德关注的点是展览阐释手段的问题,其出发点还是希望观众能感受与理解,那么在“无字真经”一节中,博物馆经理邦普斯与人类学家博厄斯对于一张小小的展览标签的争论,却导出另一个更令人深思的议题:博物馆究竟该以何种导向为根本?
1904年,劳弗作为“取经人”,为西方世界带来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学收藏——农耕人劳作时的草鞋、街头巷尾的麻将、象棋,甚至是斗蛐蛐的罐子……这些中国民族学“真经”聚集一起,为自然历史博物馆三层的“中国馆”拉开帷幕。然而如果让现在的展览设计总监穿越去参观,恐怕他会气到撞墙——没有任何策展技巧和技术手段,如此密集而细致地展示中国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好比塞给观众一篇又一篇期刊论文。邦普斯终于爆发了,他向馆长建议,科研和策展应该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负责。但博厄斯极力反对,最终给出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解决方案,即在每次展览的时候分开两个馆——一个馆面向没什么知识储备的大众,另一个馆给有这方面专长或兴趣的观众。这个建议当然被驳回,且不说没有空间来“区别对待”,恐怕到时还要面临被观众投诉的境地。
故事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博物馆的定位问题,博厄斯眼中的博物馆收藏并非为了博眼球的展览,而是服务于深入的科学研究。这种理念下,展览标签被忽视。然而,邦普斯认为若博物馆展览内容与标签艰深晦涩,难以被大众理解,那便违背了其公共职能。这两种观点的对峙,反映出博物馆定位在学术研究与大众教育之间的摇摆不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博物馆已坚定地踏上了“以观众为中心”的道路。展览标签的撰写成为了一门专业艺术,专业的释展专家与团队精心雕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们深知标签不仅要传达展品的基本信息,更要以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展品背后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展现给观众。“美国博物馆联盟展览说明牌写作卓越奖”的设立,便是对这一理念的有力推动与肯定。这些优秀的展览标签,有的通过巧妙的故事讲述,有的运用富有创意的互动式表述,成功地吸引观众深入了解展品,使观众在观展过程中不再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够真正领略到文化与知识的魅力,在心灵深处与展品产生共鸣,进而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与传播。
在博物馆与图书馆展览的漫漫征途中,我们对“灵韵”的感悟、阐释方式的权衡以及定位方向的抉择,都将持续影响着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无论是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还是展览从业者的实践摸索,都在为构建更优质、更具内涵的展览体验添砖加瓦。我们需怀揣着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这一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中不断前行,使每一次展览都能成为开启观众心灵之门的钥匙,让文化的光辉在岁月长河中永不黯淡。
来源:光明网
初审:冯碧琪
复审:马田刚
终审:苏博